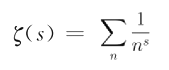文 / 刘福琪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盘踞定县城二年许,我夹在我们村七、八个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孩子群里,天天三里多地,到城里仓门口小学念书。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兼珠算老师,中等身材儿,欢眉大眼儿,要不是那张赤红脸儿,真称得上仪表堂堂。
他的姓颇为稀罕。第一次进课堂,回身在黑板上写出一个漂亮的大字:区。
“这是我的姓,我姓这个姓。我姓什么?”区老师诡秘地一笑,等待回答。
这个字一年级时语文课上学过。大家异口同声回答:“区别”的“区”。区老师开怀畅笑道:“知道你们要答错。‘区别’呀,‘区分’呀,‘红区白区’呀,是我姓的字,不是我姓的音。”区老师郑重其事地念出来,原来和‘打架斗殴’的‘殴’同音。
“啊——!”大家恍然大悟,感到长了一次学问。

这确实是个少见的姓氏,直到初中二年级语文课上学习柳宗元《童区寄传》,才又一次碰到。——还是个古人。
区老师之所以让我终身难忘,根本原因不在姓什么,脸蛋儿赤红不赤红,而在教学态度和教育理念。
区老师的温和,仅次于菩萨心肠的王省三老师。班里真有笨学生,珠算口诀,一遍一遍又一遍,就是记不住。同学们都急得火上房了,区老师还掰开揉碎耐心讲。一边开导某些不会的,一边安慰那些因早慧而性急的。临到下课布置作业时,尖子学生要完成的题目,数量小而难度大;一般学生,数量和难度一般;几个智商确实较低者,要做的问题就比较容易,但是题与题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重复性,意在使他们通过反复练习而稳扎稳打。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教育理论家,也是将“因材施教”这一最佳教学原则实施到最佳境界的教育实践家。南宋教育家程颐推崇备至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应当说,区老师的教学实践就与2000年前的至圣先师相一致。
区老师之所以让我终生难忘,更在于他对待自己的儿子与其他学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他的儿子区安华,是开学一个月后的插班生,正好和我同位。脸盘儿、眉眼儿随其父,但不赤红,白白净净,斯斯文文。
那个时代的小学生,开学初买了新书新本,都要在扉页的右下方,端端正正写上自己的姓名,姓名之下还要缀一个“记”字。区安华天生几分聪明相,但偏偏记不住这个“记”字,多次因记不住这个“记”字吃苦头,吃了苦头还记不住。
开学伊始,升旗仪式之后,全班同学首先各就各位,把新书新本一样一样放到书桌正中,接受检查。凡有书写位置不对、字迹潦草或根本未写者,区老师严肃地或微笑着一一订正,有时还幽默一两句,逗得周围同学都笑。那时没有钢笔,更没有圆珠笔,一律铅笔,橡皮一擦,什么错误都能改过来。检查完我的,就该区安华了。我立马感到,我的同桌紧张得气不敢出。语文、算术和珠算三册书、三个本,六处签名。区安华几乎没有一次百分之百正确。不是位置不对,不是书写草率,屡教不改的错误是姓名下边不写“记”而写“说”。如果百分之百正确,区老师面无表情地继续检查下一个,从不夸个一言半语。出现一个“说”,区老师的手指点书桌一下;“说”出现两个,书桌点两下。检查尚未完毕,区安华已经伸出了右手。区老师随身携带的教鞭举起,几个“说”字几教鞭,然后语气平静地说:“我打的就是你的没记性。”打过之后,区安华一边揉搓被打手心解疼,一边把“说”改成“记”。从来不掉泪,甚至没有一丝委屈表情。其实,区安华很聪明,每次放假前张榜公布成绩,他没出过前三名。大家都认为,“说”“记”混淆,那是打怕了。
教鞭者,二尺长、手指粗一根藤条也。其功能有二,一是延长老师的胳膊,便于在黑板上指指点点;二是惩戒越轨犯规学生。藤条实心,打手心特疼,又不会致残。但区老师的教鞭,对其他同学,似乎只起延长胳膊的作用,第二个功能很少发挥。
1947年正月初二,解放军准备花三天三夜拿下定县城,没想到三个小时就解决战斗。
春节以后按日开学。一进校门,大家马上发现,老师还是那些老师,但气氛大变。星期一早晨不再升旗,上台讲话的不再是校长而是一个头戴灰军帽、腰扎宽皮带的张同志。开始大家还以为“同志”就是他的名字,很快知道,“同志”适合任何人。
张同志讲完话,我们二年级进入教室,区老师一如既往检查新书新本的签名情况。轮到区安华,又有二处将“区安华记”写成了“区安华说”。他习惯性地伸出了右手,手心向上,等待父亲的教鞭落下来。因为紧张,他根本没注意到,教鞭破天荒第一次没在父亲手里,教鞭无声地躺在讲桌上。父亲的手指,在儿子的课桌角连点两次,但站立有顷,似有话说而终未开口。当父亲缓慢走向下一个待查同学时,区安华哭了,连连抬起袖子抹泪。不是因为感动,是他懂得父亲心里憋屈。
我不合时宜地开了个玩笑:“定县解放了,你也解放了。”
不料区安华瞪了我一眼,气乎乎地说:“你懂什么!”
后来获悉,张同志早已颁布铁令,新社会,新规矩,老师不准惩罚学生;谁惩罚学生,谁负惩罚学生的责任。任《论语·季氏》讲了一段小故事。陈亢误以为孔夫子也许会给自己儿子孔鲤“吃偏饭”“开小灶”,私下讲授一些其他学生听不到的学问。一次,陈亢拦住孔鲤一问,方知也不过《诗》与《礼》而已。于是,“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区老师不仅远其子,更严其子,厉其子,让儿子独享藤条子炖肉。
怎样评价“君子之远其子”,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我之所以终生难忘区老师,恰恰因为他远其子。
语曰:“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当今之世,许多家长,爱子而不知如何爱。如果有通天梯,他们会冒死一磴一磴往上爬,为的是给孩子摘星星,取月亮。如果不慎跌下来,摔个半死,孩子很可能冲上前去,狠踹几脚,帮他或她完成死亡全过程。
每念及此,我会愈加怀念区老师。
(2019.5.14《中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