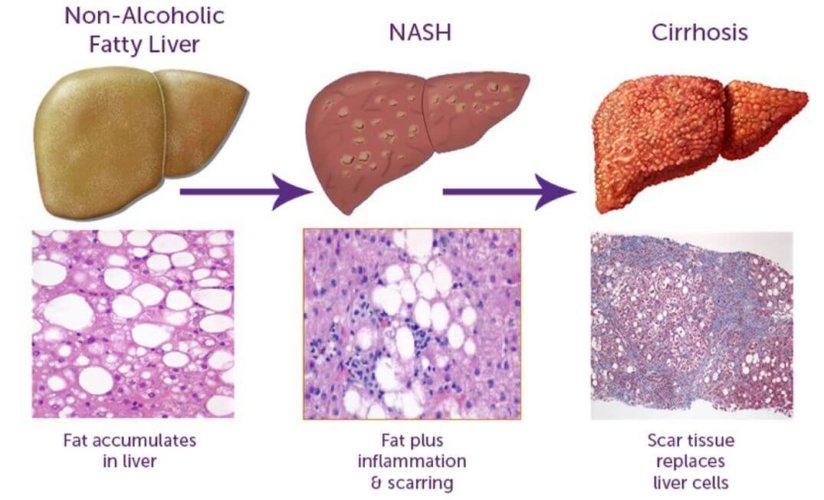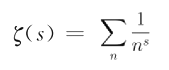文 / 刘福琪

解放以前,除了大镇子、普通村庄没有学校。不是没学生,是没钱,办不起。我们村八、九个年龄和身材都参差不齐的孩子,天天来回六、七里,到河北定县城里南大街仓门口小学念书。
有一个老师,姓周,教什么课记不得了,反正负责抓纪律,大家都怕他。瘦高个儿,国字脸儿,时刻眯缝着两只近视眼儿;冬天穿棉袍儿,春夏秋三季穿大挂儿,从来不见短打扮儿。除了吃饭睡觉,袖筒里一把铜戒尺不离须臾,须臾不离。下课铃一摇,周老师就会在院里没事人似的转来转去。看到谁歪扛着帽,趿拉着鞋,不干不净骂脏街,立刻走过来,以一种不高不低、不愠不怒的声调口出一个字:“手。”犯规的学生乖乖地伸出右手(左撇子大多伸左手)。周老师袖筒里的铜戒尺脱袖而出,啪啪啪三声响过,这才明告你为什么打你。日子一久,“铜戒尺”成了他的外号。全校七八个老师,唯独他有外号。走遍定县城,都知道仓门口小学有个“铜戒尺”,“铜戒尺”自己也知道他叫“铜戒尺”。
每星期一早晨升国旗,这是一年四季不变的成规。全校四个年级四个班,列队入场。国歌(三民主义歌)朗朗唱,国旗缓缓升。国旗图案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什么意思,长大以后才清楚。国歌句句四个字,押韵顺口,但艰深晦涩,古里古气不明白,也是长大以后才明白。但有一点,从一年级至四年级,是人人都清楚明白的。升旗仪式一开始,全校师生一律面向国旗立正,站直,行注目礼。即使你当时正在大小便,也得闻着臭味站在厕所里。因为国歌声中还走动,不少人就挨过“铜戒尺”的铜戒尺。“铜戒尺”的捡查范围不限定于学校,星期一升旗唱歌时间段,他可能游走于学校附近的大街小巷,专门检查迟到的学生听到国歌后是不是跨步到路边面向学校站立不动。
那个星期一早晨,大雨倾盆,道路泥泞,不仅我们村的所有学生,连家住南关的孩子也有迟到的。一人披一条麻袋片,一人成一只落汤鸡。校内响亮的国歌开始高唱,但大家继续歪三趔四往前跑,没有谁停下来朝学校方向行注目礼。我个矮体弱跑在最后,似乎瞥见五庚包子铺门前一把雨伞下一个瘦骨嶙峋的人像是周老师。但大家都不停下来,我停下来干嘛?进入校门,升旗仪式已经结束,哆哆嗦嗦地各回教室。万万不料,“铜戒尺”挨门串,落汤鸡一个一个都被叫了出来。雨还在下,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十几个学生,或者说十几只落汤鸡瑟瑟发抖,一是冻得,二是吓得,三是气得。这么恶劣的天气你还不破个例?周老师也瑟瑟发抖,灰布大挂紧贴在身上,两块肩胛骨像两把三角板,脑袋两侧左右对称着。
袖筒里的铜戒尺脱袖而出,但“铜戒尺”却没有说出那标识性和预报性的一个字——“手”,而是前所未有的一通长篇大论:“今天免打,因为雨大得超常,你们衣服都湿透了。可是,我的话也必须说透。”
“你们当中,年级高的同学都知道,两年以前,这根旗杆顶上挂的是一面日本旗,膏药旗。周一早晨升上去,周六下午降下来。老师、学生得哇啦哇啦唱那怪腔怪调的日本歌。我是老师,我的神圣职责是教育学生爱我们自己的国家,爱我们中华民族。眼看着高药旗往上升,我的眼泪往心里掉。”
“好不容易,日本鬼子滚出了中国,我可以真正当一名为国效力的教师了。你们抬头往上看,我们一星期升一次、降一次的旗子,怎么说也是我们自己的旗帜啊。”
大家仰头上望,细雨蒙蒙中,那面青天白日旗,湿漉漉一动不动。
周老师的训话还在继续:“这面旗帜,也许挂不了多久。但不管更换一面什么旗,总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旗,总能鼓舞全国同胞万众一心,勇往直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亲兄弟之间,不论怎么打,总有言归于好的一天。不管什么党什么派当政治国,总不会往火坑泥潭里领我们,总是想让我们穷苦了几千年的炎黄子孙走上一条国富民强的路,扬眉吐气的路。我知道你们恨我,叫我‘铜戒尺’。你们知道吗?铜戒尺打在你们手上,疼在我的心上呀!”周老师说到这里,哽哽咽咽说不下去了。我们抬起头来,但见周老师清癯的脸颊上,泪滴伴着雨滴向下滚动。我立时觉得,一股热流从心际升起,因寒冷而瑟瑟发抖的躯体霎时间反倒暖融融的了。
不到两年,定县城解放,作为国旗的青天白日旗,一去不复返。1949年10月1日,四颗小五星环绕一颗大五星的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升起。河北省定县城内仓门口小学,周一早晨升起、周六下午降下的旗帜,自然就是另一面国旗了,直至今日。
年岁愈大,愈觉当年的周老师:身体瘦削,但思想丰富;深度近视,但目光远大;行若冷酷,但感情细腻。感谢周老师,感谢他的铜戒尺。
(2019.5.6《中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