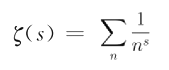文/ 刘福琪
解放以前,我在河北省定县城内仓门口小学念书一年半,教音乐和体育的那位女老师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也最美。老师姓李,那时学生不能问老师的名字,老师也不告诉学生自己叫什么。一年四季,李老师总是旗袍,深浅素艳,大花小花,根据季节与天气而相宜变换。肤色微黑,不施粉黛,短发过耳,爱笑,两个深深的酒窝好像固定在嘴角似的永不消失。
李老师不大适合教体育,不知为什么,校长偏偏安排唯一的女老师担任全校四个年级亦即四个班的体育课。好在没有任何体育器材,用不着做任何示范动作。每堂体育课,四个年级的体育课,变着花样做游戏:丢手绢,找傻瓜,耗子过街,老鹰抓小鸡;要么接力跑,学生按单双号分成两列,院东台阶为起点,院西小门为终点,从头至尾,一个接一个。体育课上,李老师经常不自禁咯咯地笑,引逗得没课的老师们不自禁走出办公室。她笑学生们,老师们笑她。
大家都盼着上音乐课。李老师的嗓子又脆又甜,不知道跟她爱吃定县本地产的绿皮红心水萝卜有无关系。李老师教的歌曲,以今天的政治和思想标准衡量,瑕瑜参半。有的仍可取,有的堪商搉,有的就该否定了。《大饭桶》歌词四句:“从前有一个大饭桶,科学知识全不懂。老天下了一场雨,他说是老天爷伤了风,伤了风。”——鼓励孩子学习科学,美学价值永存。《小徒弟》也简单易学:“你猜猜,他是谁?他是煤铺的小徒弟。又担煤,又挑水,人家叫他煤黑贼。”——这不是在宣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吗?
教唱《松花江上》之前,李老师首先讲了一个故事。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到陕西后的某一日,一个文工团前来慰问演出。一曲《松花江上》,唱得东北军将士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当台上几十名演员含泪高唱“爹娘啊——,爹娘啊——”时,台下哭声震天。枪举起来,臂举起来,口号声如巨浪滔天,如狂风大作。
“打回老家去!”
“不作亡国奴!”
“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
不分军人和百姓,不分演员和观众,青筋暴突,热血奔涌,爱国激情把所有在场人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

故事讲罢,开始教唱。有刚才鼓荡起来的激昂情绪作基础,随着李老师珠圆玉润的乐音和凄婉悲怆的节拍,同学们全身心进入浩渺无垠的艺术境界。
“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在一堂”,这撕心裂肺的最后一句呼唤,余音袅袅,在岑寂的校园上空久久飘荡。
后来我想,李老师可能不知道,这首悲壮歌曲的作者张寒晖,正是河北定县人,祖祖辈辈就住在距她教歌的教室五里之迩的西建阳村。后来我又想,李老师可能更不知道,张寒晖是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创作这首抗日歌曲的。如果李老师知道而毅然决然教学生放声高歌,那么我对李老师就不仅是喜欢和热爱,而陡然增加了钦佩和崇敬。敢在国民党磐踞的地盘,在青天白日旗下,全身心投入地教唱共产党人谱写的音乐作品,那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呀!
从八九岁时学会这首哀婉凄楚又回肠荡气的救亡歌曲到于今,七十余年间,只要不干扰别人,我得便就唱,常常感动得自己热血奔涌,热泪盈眶。
定县城改天换地以后,李老师接替区老师担任了我们班主任,并教我们语文课。万万不料,班主任没当完一学期,语文课没教完多少篇课文,我就给李老师惹下了滔天大祸。
(《中老年时报》2019.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