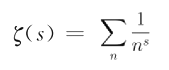文 / 刘福琪
渥太华的高山滑雪场只去过一次,而且仅仅从旁观望,但其壮阔的场面、浩大的气势、热气腾腾的氛围,永远清晰如昨。
十一月末,十二月初,两场大雪过后,渥太华郊区六个高山滑雪场相继开放。许多家庭都选择合宜的日子,披星去,戴月归,高山滑雪忙一天。回来的路上,往往只有开车人聚精会神开车,坐车的大人孩子先后沉入梦境。

我有两个女儿,两个家庭八口人。每年冬季,十个星期六划归雷打不动的高山滑雪日。去年严冬某清晨,我们老夫妇,兴冲冲随同前往某滑雪场一看究竟。
车程一小时,进入滑雪场地界,冰雪覆盖的草地上早有乌压压数百部各式车辆趴在那里。老大一片简易而坚固的木板房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赶集上店过庙会一般。全副武装的滑雪健儿,无论大人与孩子,体态臃肿、笨不即即、花花绿绿地出出进进。湿乎乎的地面上铺着厚厚的干草,干草也湿乎乎的。商店好几处,统统围绕“滑雪”一个词:滑雪服、滑雪板、滑雪鞋、滑雪竿,想租者租,愿买者买;麦当劳、快餐店、冷热饮、炸薯片,饥餐渴饮,随时满足你的需求。
更衣室里更罢衣,穿戴整齐的大小八口人,墨镜罩眼,个个判若两人。要不是四个外孙男女鸟雀似的喊姥姥,叫姥爷,真认不出谁是谁。从后门走出木板房,眼前的景象让人精神一振。百米开外,一面白皑皑的雪山高耸入云。自山顶到地面,时缓时陡的四条宽阔的滑雪道上,滑雪健儿的身姿时疏时密,一个个离弦箭、脱钩鱼一般飞驰而下。起初只是小小的点,是大人是孩子,分辨不清;红黄兰白,连滑雪服的颜色也区分不出。滑过半山腰,看出了人形和体态,头盔和服色;越往下滑,越具欣赏意趣:脚下的滑雪板如同水面上两只乘风飞动的扁舟,各个脚踩两只船;手中的滑雪竿多像弄潮儿两柄刺水戳浪的竹篙?待分清了男女、区分出大小、欣赏到红扑扑脸色和亮晶晶汗珠,风姿绰约的滑雪人已经冲到了面前。四条滑雪道,四条大角度倒悬的河,产生“黄河之水天上来”之类联想,毫不足怪。
上山必须坐缆车。四条缆车道,一天忙到晚。从木板房到山脚,是平坦的开阔地,铺着粗沙也滑溜溜的。气温接近零下30度,但人人头部热气蒸腾。从山上“飞”到平地的年轻人和小孩子,热气缭绕于脑门,那是热汗蒸发;瑟瑟发抖的看客,白气发自口腔,那是呼出的热气遇了冷。不少像我们老夫妇一样的老夫妇,像我们一样小心翼翼地在滑溜溜的粗沙地上笑嘻嘻慢腾腾踱步,边踱边跺,估计也是来观看自家隔辈人滑雪的。但自家隔辈人一上了缆车,就只能观看陌生的大男小女潇洒的风姿和娴熟的滑雪技艺了。转身四下看,无处不是激情燃烧的人。
临上缆车前,大女儿再三叮嘱一家人,中午12点,木板房里麦当劳前会合。说如不约定,临时找人难上难。她还不伦不类地引用了孟子两句话,说一经分散开来,各上各的滑雪道,自找自的滑雪群,就会“父母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只有泊车是免费的。入门要收门票,学滑要交学费;可以买日票,可以购月票;可以预付若干次。不过价码不高,谁都花得起。据工作人员讲,从上年11月底至下年3月末,每天大约四、五千人次来此滑雪健身。
我爱凿死铆,算了一笔账。按一天4000人次计,三个月滑雪期36万人次;渥太华六个高山滑雪场,每年冬天,大约216万人次参与高山滑雪。这还是缩小了的数字。而渥太华的人数,迄今刚满120万。这却是往高处估算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