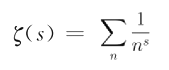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科學會證明我說的實話
文 / 陳彥伶

媽媽,我對您說,我真的最愛您。這句話是如此蒼白無力,有誰不愛自己的媽媽?是的。我已經到了耄耋之年,卻頻繁地想我的媽媽。有時想到痛彻心扉。其實她是我的養母。
我一生不知道誰是我的親媽親爸,從沒有過想念。如果我有親生父母的思念也是輕輕地一縷青烟,不知飛向何方!
養母,也許她不是一個完美的母親,但是對我的愛是全心全意的。我所有的要求,不管合理不合理,只要她能做到的,沒有她不滿足的。她對我沒有任何要求和義務,只是給無限的關愛。
可以説,我是被溺愛長大的!被過分寵愛的孩子遇事不懂好歹,我是其中一個。一個很小的例子,大約在上小學的時候,看到街上流行褲裙,就是外表很像裙子的短褲,運動與騎車都很方便。我腦筋一動,認爲把裙子從中間分開,不就是褲裙嗎?於是回家找出我的裙子,拿出剪刀,把我的新裙子下擺一分爲二,並用我的粗針大綫縫起來。你想一個十嵗孩子的活計,只能是破壞。我卻興高采烈地穿上跑去找媽媽,媽媽看我做的褲裙。媽媽正在與街坊談話,鄰居睜大眼睛看我的胡鬧。媽媽一口溫柔的京腔,這個孩子真敢下剪子,我可沒有這麽大膽子!笑眯眯示意我,玩去吧。別人都以爲晚上回家一定挨批或挨打。其實沒有,媽媽好像忘記了。這專利作品很快失寵,被我扔到一邊。更有甚著是我與男孩子一樣淘氣。幾次媽媽看見。嚇得腿都軟了,捂著胸口輕輕地喚我下來,摟著我。平時更無微不至的體貼,冬天起床,要把棉衣烤熱了給我穿……説不盡的母愛。
母親是破落皇族的一個格格,進而成了國民黨的一個官太太。到解放後,被視爲反革命家屬。這兩種身份的過度也是不容易的。爲了配合父親的改造,趕火車去郊區做力工。早起晚歸,給工廠燒鍋爐,四五十斤重的蒸餾水大瓶子,她要搬上搬下。終於她累的得了心臟病而住院。苦勞力不幹了,政治的壓力繼續摧殘她的心臟,直到令人膽寒並觸及靈魂的文化大革命革。母親心中的苦楚,我其實並不真懂。
她病了想吃口餛飩,這是媽媽常做的,可她不能做了,我給她買。可是這普通的食物也不是每天都能買到的,看到瘦弱下去的媽媽,我給她到處尋找,終於幾天内她都吃到了。記得那天她端起碗笑著對我說:“你會慣壞我的!”我立即慚愧地流淚滿面。比起媽媽對我的關照,我百分之一都做不到。我記得媽媽病還沒好,聽到街坊說外面推車賣一種南方的食品,立即起身扶著墻給我買了很多。說我們家“小弟”愛吃。這個“小弟”就是我,一個被寵壞了的熊孩子。
1967年的夏日酷熱,造反派武鬥加劇熱浪,她住院了!媽媽心臟可能已經脆弱到了極點,我本應該意识到這是媽媽的危險時刻,可是我沒有意識到,我不懂事!晚上11點多,我扶她下床小解后,我還像以往那樣,可是她突然心力衰竭,醫生也無回天之力。我腦子空空的、木木的走回家取衣服。可是家裏哪有一件像樣的8成新的衣服,拿著衣服回到病房,給母親擦身整裝,給她洗臉梳頭,然後抱她上了醫院那種可以推走的床。走廊裏昏黃的搖曳燈光下,我附在她的身上止不住地哭泣。
母親死了,我痛徹心扉,内疚是一把尖刀似的不斷地讓我痛不欲生,我的腸子都悔青了!我怎麽就不知道好好保護媽媽。她是心臟病,怎麽就不能平時多做家務?對不起,媽媽!一切都無用了。如果能讓媽媽活過來,還有什麽我不能付出的吗?可是在母親活著的時候,我怎麽就那麽傻!她病了我著急,可是媽媽病一好,我就依然如故,天下太平。很少在家裏陪伴媽媽。我捶胸頓足,打我自己!
一周后,一家三口奔向火葬場。當一切手續辦好之後,在爐前,她還是那麽平靜,似乎要睜開眼睛給我說話,我給媽媽深深一鞠躬,我感到一股扎人霉味,吸到我的心肺。人就此完了嗎?從此陰陽兩隔。
我緊緊地抱著,遞到我手裏的骨灰盒,放到我床頭,我編了個小花圈放在媽媽的照片下,兩個小花瓶插上松枝。愿媽媽永遠與我一起。
做完這一切,我躺下了,不知何时入睡了。但是我聲明:我要講媽媽死後對我的護佑,也許你們不信。
一,摸著媽媽的骨灰盒,好像她在我懷裏。聽到門響,驚喜!媽媽進來了。我連忙說,媽,您不死了嗎?媽媽說,小點聲,我是偷著跑回來的。是的,她的女兒只身住在家裏,父親在外地的工廠住,她能不擔心嗎?我把她藏到她和爸爸睡的大床上。我帶著安心的滿意睡了!這是從火葬場回來的當天。
二,後來我結婚了,不願意住在這被歧視之地,然后搬到很簡陋的平房。什麽東西都沒有拿,僅僅用自行車後面拖一個手推車,搬走了我的生活用品。搬家后,丈夫因兩地生活,回到他工作的地方去了,我一個人住在這兒。晚上媽媽來了,走得很累,頭髮都有點凌亂了,進門就說:搬得好遠,讓我好找。然后就順便就躺在我的小土炕上。我知道媽媽不放心我,來照看我。這是1970年夏天。
我在這個房子裏生了二個女兒,經厲了海城、唐山地震。一個人帶著兩個孩子過日子,忙忙碌碌的到了1979年春節。這幾年我們一直在辦理孩子爸爸的調轉,沒有音信。寒假我們準備去奶奶家過年,我們一家4口人到山東農村……
三,在農村,晚上我哭醒了。媽媽來告別,她腋下夾著一個包裹,告訴我她要走了,我忙問您去哪?她説去河北。我忙說等等我,我也去關内,咱們是一個方向,可媽媽沒有等我,徑直進入檢票口。我回頭立即買票,可是售票处的窗口立即關閉了,我使勁敲、大聲喊,我哭醒了!不明白爲什麽媽媽離開我了。這麽多年了,媽媽一直跟著我的。這是1979年的二月。
從奶奶家回來才知道,我做夢的那天,調令已經到了。孩子爸爸調到我們身邊了!
媽媽以爲有了丈夫就不用媽媽了,丈夫哪有媽媽好?從那時到今天42年過去了,我再沒有夢到媽媽。我摯愛的媽媽!
感激您如此護佑我12年(1967-1979)。有時我想我不配的。
我永遠思念您,愛您。永遠!——您的“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