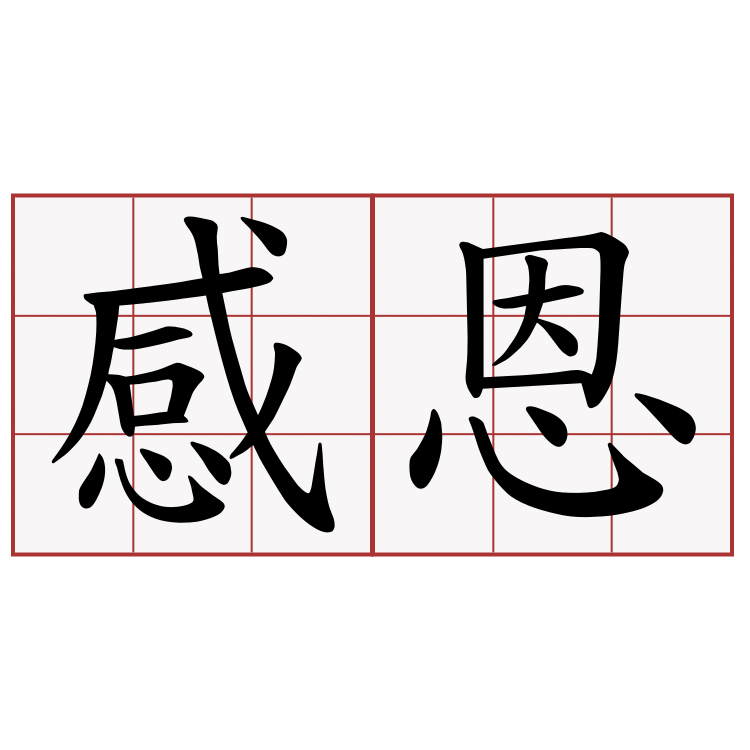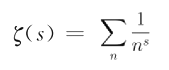文/ 刘福琪
1947年正月,河北省定县城解放。后不久,各村先后建起自己的小学。我们中军帐村小学,占用一户富农闲置多年的三间土坯房。打通隔断,就是教室。两端各砌一个二尺多高的砖垛子,上面搭一块一尺多宽的长长的木板子,就是课桌。从前到后,这样的课桌五、六张。低年级人多,占两张。坐什么?小板凳有高有低,有宽有窄,有新有旧,有的坐麦秸编的蒲团上课。外面一个半亩大小的院子,放学整队,唱歌比赛,胡打乱逗,都在这片天地。一个老师,一间教室,四个年级如何教?城里的孩子,当时当代就闻而撇嘴。现今的孩子们,除了张艺谋导演的《一个都不能少》里那样穷苦地区,会以为是天方夜谭。岂知我们那个时代,千真万确就那样上过课。当然,说“年级”有点冠冕堂皇,其实一个年级三到十人而已。
常说急中生智,穷中也能生智。各村同样穷,各村老师于是生出同样的智。同一节课,四个年级各有营生。有的复习,有的预习,有的写作业,只有一个年级听老师讲新课。新课讲到一个段落,开始写作业,刚才预习的年级转而上新课。互相干扰是司空见惯的,因互相干扰而出笑话是屡见不鲜的。比如,一年级一个学生骂另一个学生娘,被骂学生的哥哥在三年级,跑过去就是一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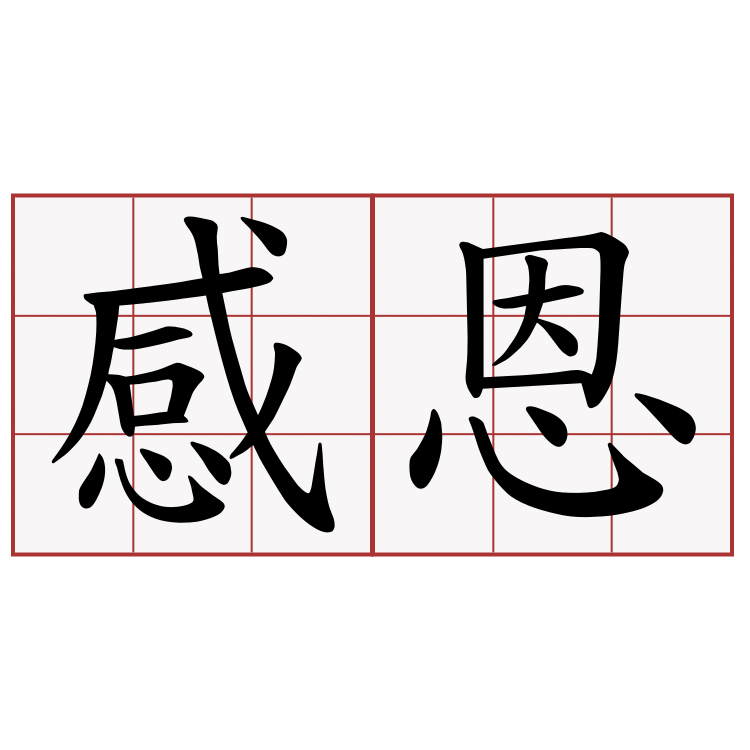
为管理方便,村委会指派两名有点文化的人担任领导。一曰校董,一曰教文。校董负责教学秩序,教文掌管一应财物。有顺口溜:“大校董,二教文;三尿憋子四脚盆。”尿憋子者,夜壶也。脚盆亦非洗脚盆,尿盆也。
校舍有了,但没老师。村委会就让地主分子高老宾充任。高老宾有发家经验,哪里上过讲台?村委会想的是秃子当和尚——瞎凑合,有胜无。高老宾不然,给个棒槌就当针(真)。土改时留给他家的磨房就成了他的备课室,昏黄的豆油灯,往往亮到半夜三更。没有教材,四个年级都讲些什么,他得费尽心思,反复琢磨。他家是村里唯一一户地主,他是全村唯一一个地主分子。他自编自教的语文教材,左得很,革命得很。不是觉悟高,是警惕性强。有一首歌,不知他从哪里学来的,我至今会唱:“国民党啊,(那个)一团糟啊!一团糟啊一团糟啊,坏蛋分子可不少。事变前,它压迫咱们老百姓;事变后,干的坏事更糟糕……”如此左得无懈可击,也没能保住他平静平安的处境。三、四个月后被革职。县里批评村里:“让地主分子当老师,等于让他为国民党反动派培训生力军。”
第二位老师是高老宾的侄媳妇陈开平。解放前夕,精明的陈开平劝说丈夫高砚山,一顷地几乎全部白给似的去(卖)给了佃户,土改时划了个中农。自家只留下村头五亩水浇地,图个来去方便。地主家的媳妇,没有一个不俊。陈开平欢眉大眼儿,细皮白肉儿,特会来事儿,全村男女老幼,没有不说好的。当上老师以后,比叔叔高老宾更受学生欢迎。嗓子也脆甜,不亚于定县城里仓门口小学的李老师。那个时候,全国尚未完全解放,特务分子非常嚣张,到处游走不定地搞破坏。陈老师教过一首歌,单道抓特务:“天上鸟儿过,地上影子飞,特务分子你欺哄谁?你呀欺哄谁?赶快到政府,认啊认你的罪。”陈老师娘家与我们村三里之隔,乃颇有名气的大地主,陈老师料定迟早会牵连到自己。通过熟人,教书三个月后,北上保定市当上了会计。因为待人诚恳,助人为乐,历次运动平安无事。
前两位老师,各在我的印象里留下了一首牢记终生的歌。第三个老师是我的大表哥,教课不满半年,只将一个小笑话刻在了我的心板上。
大表哥是我二姨的长子,称得上本村高家一个小人尖子,小学没念满,就跟一个表舅到八路军一家花纱布公司当上了业务员。60多岁时闹了个离休,资格就来自于此。至今也不明白,算是参加了革命的小业务员,为什么脱离了革命,回乡当了一段小学老师,而后又重归革命队伍。
这个小笑话,是说一个私塾先生赴了一次宴席。穷惯了,鸡鸭鱼肉,胡吃海塞。一边往回走,一边划拉肚子念叨:“老天爷,你往下行啊。你要不行,我可不行啦!”一阵风来,礼帽被颳到地上。吃得太撑,蹲不下身,弯不了腰。恰好一个妇女走来,于是央求道:“大姐姐,劳你大驾,帮我捡一下礼帽吧!”妇女不仅不帮忙,竟还恼羞成怒,破口大骂。私塾先生一看,人家肚子比他的还大,奇怪地问:“我去赴宴啦,你也去赴宴了吗?”
(2019.5.28《中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