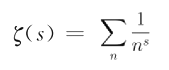文 / 刘福琪

孙老师也是我们村办小学史册上一名老师,但走马灯转到孙老师来校就停止转动。“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孙老师在我们村任教近十年。
孙老师单讳一个“明”字。来村报到时,年届不惑。匀溜溜的身材,白皙皙的肤色。家做裤褂随季节和天气相应更换,但头上一条白羊肚手巾,只有上炕睡觉才摘下来。
孙老师有备而来,对中军帐村小学一盘散沙的情况已了如指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孙老师“下车伊始”,首先立规矩。没有铃可摇,没有钟可敲,孙老师以哨声为信号。哨子一响,上课,下课,集合,放学。上课哨声吹罢,同学各就各位。老师走入教室,班长(其实乃全校四个年级的总指挥)朗声喊“起立”。老师走到讲台前(其实没有讲台,象征性),严严肃肃一鞠躬,说:“同学们请坐。”大家一落座,正式上课。
一间教室,四个年级。同一个时间段里,复习的复习,预习的预习,写作业的写作业,只有一个年级听老师讲课。前几任老师上课,深浅难易,全无所谓。孙老师安排课,无论语文和算术,课前都形成教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的系统性和时间的利用率。
下课时,孙老师平静地道一声“下课”,班长喊“起立”。大家起立,老师规规矩矩鞠一躬,半亩校院立即欢腾起来。
过去放学无章程。最后一节课一到点,四、五十个学生如鸟兽散。孙老师当天立新规。按照东南西北四条街道,面向教室列队四行。班长的“向前看齐”、“向前看”等口令,人人恪遵。班长见队已成形,喊声“立正”,再喊声“稍息”。孙老师走到队前,说一声“诸位同学”,全体立即变“稍息”为“立正”。孙老师说一声“稍息听着”,大家变“立正”为‘稍息’以后,孙老师作全天的总结。总结结束,在班长指挥下,一队一队出校门,不到家门不许离队。
孙老师来时,我正念三年级。全年级三个人,大柱哥比我大三岁,振林叔比大柱哥小一岁。从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固定的年级始,凡寒假、麦假和暑假,期末考试后的奖品如铅笔、橡皮和笔记本之类,全部归我。孙老师对我自然是宠爱有加。一天放学后,特意把我留下,笑眯眯地说:“刘福振,名字太俗,我给你改一个吧。‘振’改成‘琪’,怎么样?琪,一种宝玉呀!”我说不出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也没见过宝玉什么样,说回家跟大人商量商量。父亲淡淡一笑:“成不成气候跟名字无关。不过就听孙老师的吧。”从此至今,我就开始叫刘福琪。数十年间填写无数次表格,“刘福振”就填在“曾用名”一栏里了。
回顾一生,从解放前步入小学直至62岁超龄退休,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未遇到多么艰难的崎岖路,更未曾攀爬过不去的火焰山。那个年龄段,农村孩子上大学,也算得上凤毛麟角;在大城市天津当教师,足够农家子弟垂涎三尺;何况后来忝居于大学教授之列,更让家严家慈脸上有光。如此等等,是否叨了孙老师改名字的光?但是,概括一生,虽顺顺利利,却也甘苦备尝;虽平平安安,终属平平庸庸。这是不是吃了孙老师改名字的亏?福也罢,祸也罢,现在全看淡了。还是苏东坡讲得透:“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村里成立识字班,扫盲。孙老师晚上没事,自告奋勇当上了妇女夜校老师。
孙老师家在40里开外的大吴村,除了寒、麦、暑三个假期,一般不回家。正当中年的夫妻两个,就这么天各一方,牛郎织女。每天夜校下课后,总有那么几个求知欲旺盛的姑娘和媳妇,迟迟不走,围着孙老师询问一些深奥的疑难问题。比如“兄弟”的“兄”怎么会当“哥哥”讲?
日子一长,孙老师的绯闻开始传出来,说他跟王家一个姑娘怎么样怎么样。到底怎么样,谁也摸不太准。世上的流言,海上的波澜,孙老师不能不当回事了。他知道自己在乡亲们心目中是一个好老师,正人君子。打不倒的威信来之不易,不能就此一落千丈。据说孙老师主动邀女方谈了一次话,劝她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尽快找一个好婆家。姑娘也自筑堤坝,阻挡住感情的洪流,很快成了20里外某村的媳妇。一段似有若无又非完全捕风捉影的传闻到此结束。
大学一年级暑假回家时,获知孙老师得了绝症,两个月前恋恋不舍地回家休养。父亲买回二斤槽子糕,让我到大吴村去看看恩师。谁想还没借到自行车,孙老师去世的噩耗就传到了中军帐。
面朝西南方向,我眼含热泪,深深的三鞠躬。
(2019.6.3《中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