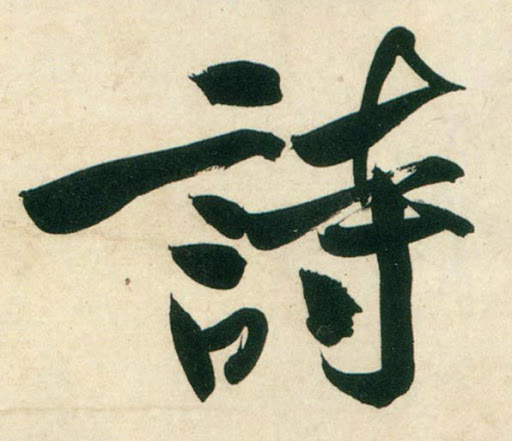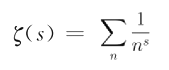文 / 刘福琪
我的初中母校河北省定县三中(后改为定县二中),与新中国同庚。定县头号大地主王老合扫地出门,王家大院就成了我们的校舍。布局完全一致的多所四合院,鳞次栉比,纵横成行,青砖灰瓦,画栋雕梁,覆压300余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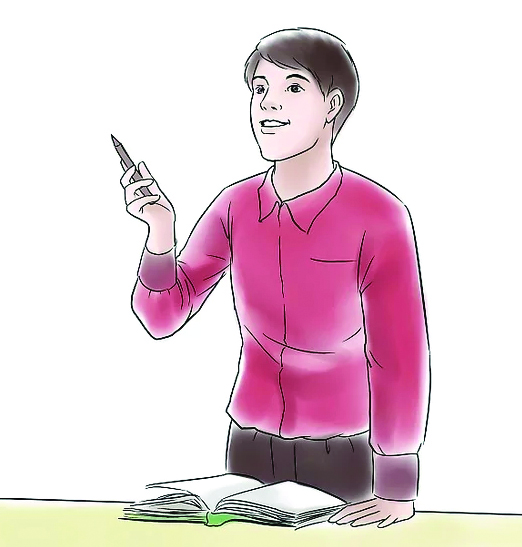
班主任王作东,原天津师范专科学校地理系的高才生。1952年暑假前,我毕业,他毕业。我小学毕业,十三、四岁一少年,成为他的第一批学生之一;王老师大学毕业,二十二、三岁小伙子,成了我初中三年未更换的班主任。王老师事业心极强。每天晚上,王老师宿舍的灯光,总是明明亮亮到深夜。出于好奇,不少同学都曾悄悄地跨上青砖砌就的台阶,隔着玻璃窗往里窥瞧。王老师或伏案书写,或专心捧读,或对着墙上的挂图指指点点。王老师记忆力超群,一登讲台就崭露头角。初一初二中国地理,初三世界地理,在我的记忆里,河流的长度,山脉的高度,矿藏的储量,农作物的产量,所有数字都百分之百准确。地理课是死记硬背的枯燥课,但王老师的课堂上,时不时也爆发笑声。讲安徽省省会合肥,他来句歇后语:“俩胖子结婚——合肥”;讲印度尼西亚,他讽刺某白字先生错念“爪哇”为“瓜哇”,还为自己辩护:“爪哇、瓜哇是一个地方”……数不胜数。
王老师脾气温和,平易近人。对于学生,无论学习、生活与待人接物的规矩礼数,巧妙开导,循循善诱,从不横眉立目,板着脸训斥。在我的记忆里,三年之中,王老师仅仅发过一次火,生过一次气,而且,事后进展之蹊跷,一直是学生们心中的不解之谜。
大约是初二下学期的一天,苏秀申眼泪汪汪地找到王老师,说他包袱里的九块钱不翼而飞了。九块钱,那是一个半月的伙食费呀!下午两节课后,王老师召开全班紧急会。一向平静儒雅的白净面皮,第一次激动得面红耳赤。他说他的学生必须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一生一世不能与偷啊窃呀这些污秽不堪的词汇有牵连。他深知农村的青少年撒不了谎,做不了假,偶尔做“贼”,肯定心虚,遂发动了一次心理攻势:“讲台上这么一站,我立刻就知道苏秀申的九块钱在谁的手里头了。我不要求你马上站出来承认错误,希望你两天以内主动找我,说明原因,道明情况,咱们烟消云散,既往不咎。但是如果你不找我,恐怕你就会被动的。”
但是日复一日,全无动静,谁也不知道苏秀申那没有翅膀的九元钱到底飞到了谁的手里。再后来,一传俩,俩传仨,人们都知道王老师代失主交上了两个月的伙食费。苏秀申失窃9元,得到了12元,也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例证。
不是没人追问,但王老师闭口不谈,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他。被刨根问底到极端,王老师便严肃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人人都要从中受到教育,甚至包括我自己。”
世界很大,有时又觉得她很小。20年后,王老师从定县调回天津,到天津外国语学校任教,跟我任职的学校近在咫尺。一次闲聊,我问及少年时期那个失窃之谜。王老师一笑,一叹,回答如下:“那个年代,农家子弟个个纯洁忠厚,朴实无华,上进心强,自尊心也强。不是磨盘子压手,不会产生一念之差。还记得那次紧急会吗?两三秒内我就百分之百知道了真相。但他没有勇气找我,老师何忍不留余地呢?真要公布姓名,他还怎么立足同学之中呢?百里挑一考上中学,可望有功于国。我不能因为他少年阶段一次偶然的过失毁了他一生。他家很穷,母亲多病,每月六元伙食费,从哪儿来呀?从事出到毕业,我一直隔三差五周济他些零花钱……”
事隔20年,无需再点名,老师絮絮一番话,我也就准确地知道了他是谁。此前多次谈话中,王老师曾就话题所及,谈到初中毕业时我们班几个去新疆“八一”农学院读书的同学。其中一人,毕业后一直工作在西北边陲,跟王老师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
此时此刻,我只觉得又一次体会到我的老师善良的人性、博大的胸怀和对学生至纯至真的深情。
王老师,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2019.7.4《中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