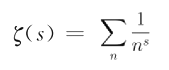文 / 刘福琪

保定一中乃河北名校,校风纯正。很重理科,人人谨记“学好数理化,天塌也不怕”;也重文科,从初一至高三,投稿之风蔚蔚然。
那个时候,农民没有富裕户。一个月六元五角伙食费,农家子弟按时缴纳的不多。我每月两元助学金,四元五都交不起。于是自高一下学期开始,打起写小说、赚稿费、替父母分忧的的念头。
七天一个星期日,人家三五成群逛裕华路上的天华景商场,添文具、买牙具,隔着门窗看看南大街一家又一家冒着热气的大锅血豆腐,闻闻白云章包子铺飘飞出来的羊肉香。我则忍住上街看血豆腐、闻包子香的欲望,一头钻入图书馆:构思。构思不出来,随手翻杂志,看人家怎样构思。偷偷寄出一篇,无情地退回来;再偷偷寄出一篇,又无情地退回来。剪去信封右上角,写上“稿件”两个字,就可免费投递,但面子是要花费代价的。好几次,有人从“学生信件存放处”走进教室,高举盖着“退稿”二字红戳的白信封,老远就喊:“福琪,大作怎么又退回来啦?”
正当我心灰意冷、准备偃旗息鼓回归常态时,《保定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高老勤卖鞭炮》。有同学打趣说:“‘刘福琪’这个俗名字,一变成铅印就精神多了。”
一摸到路径,走起来就顺了。接二连三,《保定日报》、《河北日报》发表好几篇。人心不足蛇吞象,高三上学期,我将一篇三千多字的小说《三户庄稼人》寄给河北省唯一的文学杂志《蜜蜂》。那时候,报刊界重视发现人材,工作效率也高。仅仅一周后的一个课间,校团委那位女书记跑入我们教室喊:“刘福琪,下午五点前去找一趟蜜蜂。”有人愣了,找蜜蜂干啥?为啥不找马蜂?我没愣,我紧张,兴奋。
那时保定人不知啥叫公共汽车,有也舍不得坐。忐忑不安地快走40多分钟,提前半小时我就诚惶诚恐地叩响了《蜜蜂》编辑部大门。一位女编辑把我领进旁边主任室,说:“梁主任,小刘来了。”
梁主任40来岁,敦敦实实的个儿,圆圆乎乎的脸儿,慈眉善目的。拿出我的小说,大到命题立意,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布局谋篇,小到修辞方法,标点符号,行文格式,无巨无细,详细指点。
《三户庄稼人》写那么三户庄稼人组成互助组,取长补短,互帮互助,比起单门独户强多了。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仍然能微力寡,远远经受不住老天爷发横施威,于是主动找到乡政府,要求成立更大规模的什么组织。
针对作品主脉,梁主任评价颇高,说我具有敏锐的生活洞察力,作品充分显示了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确性和生命力。临别,梁主任送给我老厚一叠稿纸,鼓励我农民子弟爱农民,学农民,写农民,一直写下去。
后来又去送过两次稿,梁主任很忙,只抽空跟我畅谈过一次。深深的感慨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见于2019.8.12《中老年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