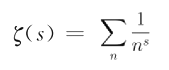文/ 刘福琪

我父亲一直经营点粮食生意,有小钱赚。我有时就顺路买俩芝麻烧饼当午饭。一天语文课上,我突然闻见丝丝缕缕的芝麻香,伸手往书桌里一摸,粗布手巾空空如也。扭头一瞅,陶红儿的嘴角还沾着芝麻粒。又惊又气,马上举手报告说:“陶红儿偷吃了我的烧饼。”
别看李老师素常亲切可爱,偶尔也严厉可畏。她常讲,人穷不能志短,马痩不能毛长,偷财窃物最可耻。
听到我的举报,李老师匆匆走过来,第一次怒不可遏。怒一不可遏,手里薄薄的一本语文书扬了起来。陶红儿下意识地一歪头,额角恰恰被墙上一颗钉子划了那么一下,鲜红的一丝血迹显现出来。李老师的办公桌上,红药水、白药棉之类常备不懈,以便学生受点小伤时救急。见陶红儿浅浅一道红印,李老师心火一变而为心疼,马上让班长到办公室取些疗伤物品。
祸就出在班长这一趟。跑出去的是班长一个人,跑回来的却是两个人。班长身后,是那个皮带不离身、灰军帽不离头的张同志。张同志是解放以后代表新政权进驻学校的第一人。不知道是什么官儿,反正连校长都毕恭毕敬地让着他。每天放学整罢队,张同志先讲话,然后才轮到校长。
此后两三天,李老师还正常来校。但郁郁寡欢,愁云惨淡。一个星期后,李老师彻底消失。虽然年仅八、九岁,但我明白,李老师的离去,肯定与陶红儿碰钉子流血有直接关系。我就很后悔,很自责,很惭愧。假如我那一天不买芝麻烧饼而一如往常带俩棒棒面饼子,不就没有香味飘散了吗?陶红儿肚里的馋虫子不就活跃不起来了吗?假如发现陶红儿偷吃了我的美味而顾全大局不举报,李老师不就不会罕见地动怒而且举起课本要惩戒这个馋嘴小猫了吗?假如陶红儿见语文书拍下来而不躲不闪,不就不会碰钉子了吗?假如发现陶红儿的额角浸出了那么一丝半缕红颜色,而李老师不加心疼,班长不就不会急匆匆受命跑向办公室了吗?然而一切都无可挽回地出现了,李老师从此不见了。但区区小事何以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这个不解之谜,直到五、六年后才得以开释。
初三最后一学期,走上语文课堂的是一位新调来的程老师。两三天后的黄昏,远远看见一位妇女手拉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孩,在平坦的大操场上慢慢溜跶。别看身穿列宁服,我一眼就认出来她是李老师,教我唱《小徒弟》、《大饭桶》和《松花江上》的李老师。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我跑上前去,颤声喊了一声“李老师”。李老师马上也认出了我,显然也高兴得很:“啊!刘福琪!你成中学生啦!”我告诉李老师,我已经是三年级,马上就要毕业。言来语去,原来新来的程老师跟我的李老师是一家子;言来语去,当初的谜团终于解开。
皮实实的陶红儿涂抹了红药水,屁事没有。偷吃人家烧饼的羞耻感维持了三分钟,随即胡打乱逗起来,哪知老师办公室里激烈的唇枪舌剑呢?
张同志姓张名威,训斥李老师道:“陶红儿吃别人一块烧饼,不是品质问题,是因为家里穷。穷人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和主力军。你痛打贫下中农的孩子,你站到了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以酒窝和甜笑一向获得老师学生好感的李老师,居然一下子判若两人,一下子将潜藏于深层的性格另一面暴露得淋漓尽致。李老师当即:“别人的烧饼不是被他吃了一块儿,而是被他吃了整整两个。吃多吃少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偷’。树小得修理,人小得调理。走遍五湖四海,‘偷’总不能说是光彩的。至于说痛打,不符合事实。薄薄的一本语文书,能痛到哪里去?”
张同志威立即宣布:“限期三天,交来检查。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李老师一字一板地说:“这种体裁没学过,也不想学。”何需三天?李老师第二天便辞职回家了。
以上这篇口头回忆录,李老师复述得心平气和,我听得回肠荡气。
拿到保定一中录取通知书后,我专程登门道别。李老师似乎比我还高兴,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硬皮笔记本,思索有顷,扉页上写下一首诗,郑重其事地递给我。
李老师赠我的那个笔记本早已不知去向。但李老师作为赠言的四句诗,没齿不忘:“要学松树不畏寒,岂做垂柳弯腰肢?鄙夷藤萝巧攀附,宁为苎蔴身正直。”
李老师,您现在在哪里啊?
(《中老年时报》2019.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