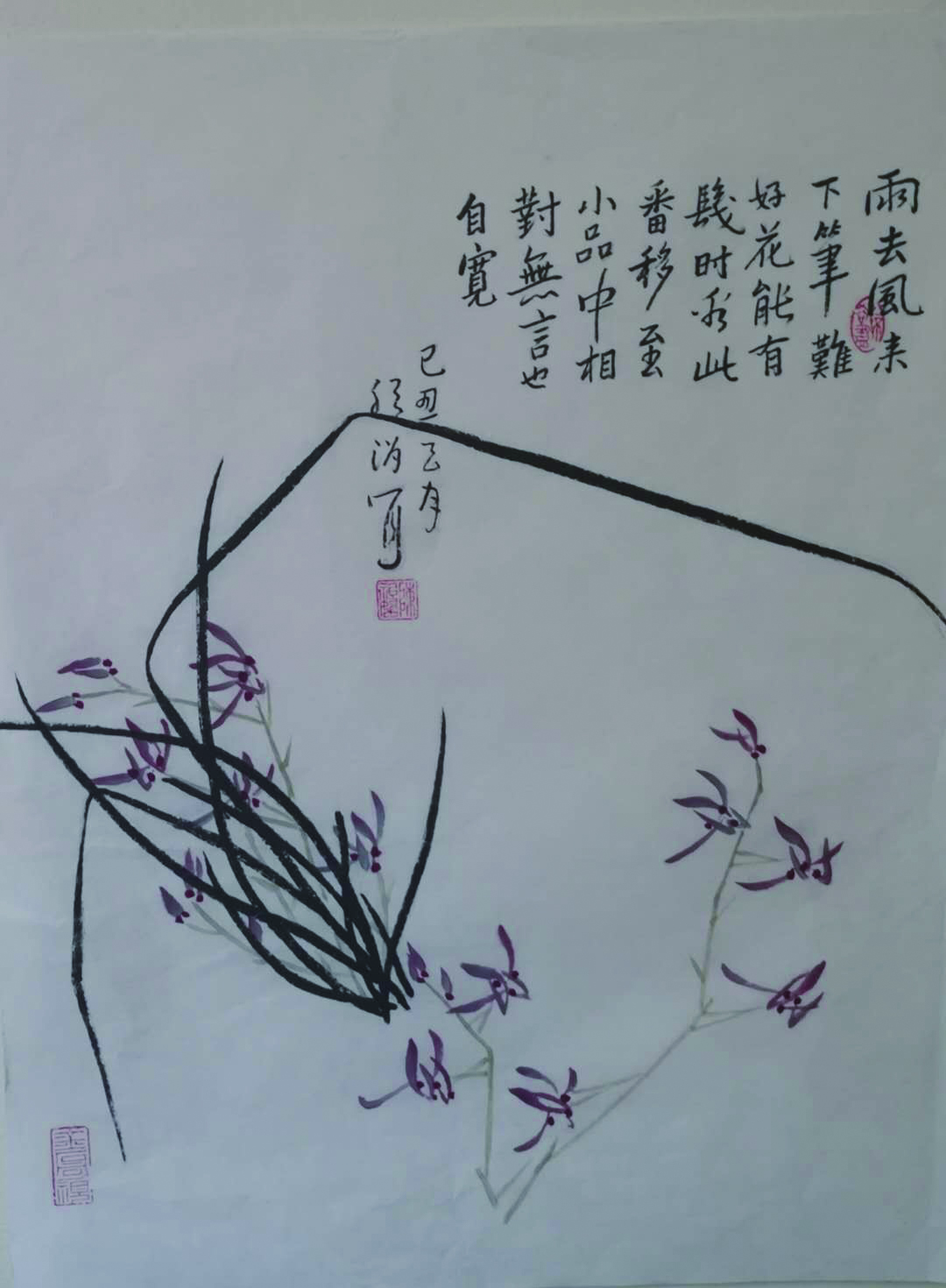文 / 郭玉秋

我们经历了中国三年灾害,我家也同样缺食少穿。1960年的春节,初一早晨,我家包不起饺子,妈妈做的是疙瘩汤,而且每人只能一小碗。爸爸端起他那一小碗疙瘩汤,分给了我们几个,他放下碗筷子离开了饭桌。我还记得父亲那悲伤的表情,他是感到,自己没有尽到当父亲,当一家之主的责任:连过年都没让全家吃上一顿饺子,要知道过年吃饺子对北方人的重要。其实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全国人们都在贫困线上挣扎,我们有什么例外。那年冬天,父亲在农村买了一卡车甜菜疙瘩,那是制造糖的原料,那里面含有很多糖。把它馇成丝,放上玉米面,蒸成团子,又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度过了艰难的一年。
我一心要考大学,因此学习比较用功,晚间看书到很晚,爸爸有时走到我的房间说,养养你的眼睛吧。因为从上高中我就近视了,开始戴近视镜,我也不知如何养养眼睛,功课没有看完,我是不能睡觉的。
我从小学到高中三年,一共12年,家里只去过学校两次开家长座谈会,一次是初中二年,我大嫂代表家长去了我上学的第五中学。同学都趴在门缝往教室里看,说着:你嫂子长得很好看。另一次是高三毕业前,父亲去了齐市一中,为我开家长座谈会。开完之后我问他,老师都说了什么?他说,老师表扬了每门功课是五分(我们那时是五分制)的学生,几乎每门功课都念了你的名字,看得出,他很高兴。高考那天,父亲开卡车送我去考场,本来我可以坐在驾驶蓬里,但是我的同学赵淑琴和我一起去,我只好和她一起坐在后大箱里。我把自来水笔放在裤兜里,由于坐在后大箱的地上,笔掉了也没发现,要进考场发现没有参加考试的笔了,只好用赵淑琴的备用笔参加考试。她那笔尖较粗,有时还不大下水,好在还勉强可以使。即或如此,回家后也不敢告诉父亲,笔丢到了他的车上。我就是用赵的那支笔考完了整个高考的各门考试。
在中国最难考大学的1962年,我考上了大学。我们那时上学,不用交学费,住宿也免费,只是吃饭和买书需要自费。很多同学都有助学金,我们班47个学生只有四人没有助学金,其中就有我一个,因为父亲的工资较高。那时家里每月给我邮寄20元人民币,大学5年,加上文革在校晚毕业两年,家里从没有晚寄钱给我。其实我家也不富裕,父母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供我读书。
文革时,学生停课,工厂停工,父亲只好在家赋闲。他既没有参加斗争谁的大会,也没有被哪个徒弟揪斗。他有个朋友是泰来县监狱的领导,每次来齐齐哈尔都和我父亲聚聚。他总是说,每次送犯人来,我都看看有没有老郭家的人,我好特意照顾。因为那时是文革时期,进监狱的人较多。他的这份好心,一直没用上,因为我的哥哥弟弟们谁也没进监狱。到了复工时,他又上班了,成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