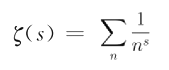文 / 刘福琪
每年四月解冻以后,十二月封冻之前,渥太华运河,有风时波澜不惊,无风时涟漪层层。水面低于地面二尺许,就那么由西向东平静地流。很少有谁驻足观望,更少有人为之陶醉。但封河期一到,平静的水面变成明亮的冰面,这条不大被关注的运河立刻成了众望所归的繁华处所,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滑冰场。擅长滑冰的男女健儿,爱好滑冰的男孩女孩,天天万头攥动,鲜艳夺目的头盔和服色令人目不暇接。开车行进在依河蜿蜒的马路上,你会产生一种错觉:蓝色的渥太华运河,怎么花花绿绿五颜六色了?无声无息的渥太华运河怎么波浪翻滚汹涌澎湃了?而且,腾起的浪花怎么箭一样相互朝着相反的方向飞逝?不识运河真面目,只缘不在此河中。一旦身临其境,即使冰面上行片刻,来来回回观望有顷,你就平静不下来了,额头冻得冰冰凉凉的同时,心头一定热热乎乎的了。

运河滑冰不同于高山滑雪,不需要驱车远征,更不需买票。渥太华运河弯弯曲曲地斜穿渥太华市区,只要零敲碎打有点闲工夫,尽可随时往还。作为一条河,渥太华运河属于渥太华,全流域都在渥太华境内,但一朝成了滑冰场,它的拥有权就归于整个加拿大了。每当周末,每逢节假,甚至请假,许多外地人纷纷驱车前来,乘飞机空降,投亲靠友住旅馆,乘兴而至,兴尽而归。
道斯湖与渥太华运河衔接处的一角,每年滑冰季节,无例外安置两间简易而牢固的木板房,一间租赁和出售冰鞋、冰刀和头盔,一间有偿供应比萨、汉堡包、冷热饮。木板房一侧,还无例外趴着两辆不同外型、不同功用的工具车,每天“寂寂黄昏后,凄凄人定初”,铲除碎屑,喷洒净水,刨光冰面。为了满足外孙男女滑冰的热望,我们老夫妇,每年都数次陪同前来。每次前来,都在两间简陋而兴隆的小店与两辆巨车旁边久久伫立,久久徘徊,观冰面,观店面。面对这个世界最大滑冰场万人飞驰的盛大场面,每次都额头冰冰凉凉,心头热热乎乎。
三个月许的滑冰期内,宽50米许的运河冰面上,从晨星寂寥至夜幕拉开,虽寒风凛冽,砭肌刺骨;大雪纷纷,飞棉扯絮,一直是左看不见头,右瞧不见尾,弥望都是明丽的亮度、飞驰的速度和强劲的力度。但蜿蜒五十余公里的渥太华运河连同五十余公顷的道斯湖,只是加拿大人的露天健身处,而非竞技场,没有比赛性质,不设比赛项目。“十个指头分长短,荷花出水见高低”。在这里,滑冰技艺的优劣高下,参差不齐,千差万别。兴之所至,我爱诌几句古体诗,姑以古体诗譬之。这里有诗圣、诗仙和诗鬼,也有俚俗浅陋的张打油。许多蹒跚学步的小娃娃,居然滑得板眼分明,“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的孤身一人,纵横驱驰,“自去自来梁上燕”;有的夫妻并驾,卿卿我我,“相亲相近水中鸥”;许多高手,飘逸潇洒,疾电迅雷,大有“更催飞将追骄虏”之概;有时成群列队的帅男靓女翩然现影,倏然消踪,“八骏日行三万里”。有一个镜头,让人倒吸冷气。一位白人青年,梦幻一样疾飞到几位“冷”眼旁观的老者跟前。不知为啥,高大身躯想直竖起来,一刹那间,仰面跌倒。不设伏笔,无过渡段,后脑勺大力度、大强度直接拍到冰面上:“砰!”小伙子安安静静躺作一个大大的“大”字,我以为大事不好。孰料同跌倒时一样干净利落,小伙子平地弹起。搓搓脑勺(估计是奇痛难忍),揉揉眼睛(肯定会金星乱迸),冲几位感同身受的大爷大妈涩涩一笑,“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俯身,扬臂,蹬腿,眨眼间融汇于色彩斑斓的浪涛中。
万顷波涛里,两类浪花令我惊奇乃至惊悚。一类刚刚“人之初”,“哀茕靡识,越在襁褓”(嵇康《幽愤诗》)。襁褓铺陈在婴儿车里,被束缚(越)在襁褓里的婴儿,嫩嫩的脸蛋冻得红红,滑冰技艺娴熟的妈妈或爸爸将婴儿车推得或拉得如鸟飞,如鱼游。一类业已“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精神矍烁或目光痴木地端坐或软卧于轮椅里,滑冰技能纯熟的儿子或女儿推着或拉着轮椅慢慢悠悠、逍逍遥遥,为的是满足一下老人“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之心。
渥太华运河的滑冰期约90天,每天约近万人,两数相乘,数字是很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