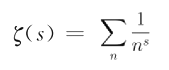文 / 刘福琪
我和文章结缘甚深。高中时开始练习写作,并且写出了点小名气;大学上的是中文系,天天读文章,学文章,古往今来的文章,汗牛充栋,车载斗量,读了不知有多少。毕业之后,教文章,写文章,毕生围着文章转,文章牵动着也驱动着我的心。倘要寻根求源,我必须由衷地感谢我高小阶段(小学五、六年级)的语文老师马伟骏。

上世纪50年代初,我们村进驻了近百号解放军,有男也有女。我家住了四、五位女兵,大者二十出头,小的十七、八岁。原来寂静的庭院,立即活跃起来。歌声笑语,伴着枣树、杏树、大杨树上的鸟鸣一起空中飘飞。星光下,月色里,她们边唱边跳:“月亮爬上了东山,营火燃烧在广场上。年轻的红军快来舞蹈,欢乐的朋友快来歌唱。”
观者如堵,掌声阵阵。除了沉睡的夜晚,整个村庄似乎都让快乐和喜庆笼罩着。
一位四川女兵陈金玉,白净净的脸儿,圆溜溜的眼儿,对我最好。她说她有一个弟弟,跟我一般大,功课也挺棒,甚至文文静静的也像我。部队的伙食特别好,上顿下顿围着“肉”字转。每从伙房打来饭,肉包子、大馒头什么的,噼里啪啦往我们家大人孩子跟前扔。金玉大姐三天两头给我本子呀,铅笔呀。一放学回家,她就笑着问我今天上了什么课,算术讲到哪儿了,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她。
但是,大约过了三个月,大队人马开拔了。临走前一天傍晚,金玉大姐把我拉到外院那棵大椿树下,抚摸着我光光的头皮说:“再见了我的小弟弟。这只钢笔和这双皮鞋送给你作个纪念。”农村的孩子有心无口,意识到此地一别,永无会期,嗓子哽咽着,嘴撇着,就是说不出话来。大姐眼里也噙着泪花。我问你们要去哪里?大姐说:“我们也不知道,知道也不能说。”
部队走后不久,传闻随即而至说他们坐闷罐火车一路北上,开赴朝鲜。刚到鸭绿江大桥就遭到美国飞机狂轰滥炸,没有多少战士幸免于难……我从此天天惦念他们,惦念那些月光下跳舞唱歌的欢乐群体,尤其惦念我那位四川大姐陈金玉。日思夜想,梦牵魂萦。
正当此时,作文课上,马老师出的作文题,恰好给了我一个释放情思的机会:《给志愿军叔叔的一封信》。边写边垂泪,边擦边疾书,一气呵成,文不加点。
下个星期发文课开始前,我激情难耐,焦急地盼望马老师富于幽默的好词妙语成串成行地施加于第一篇范文。——当然我是作者。打死没料到,“起立”之后刚一“坐下”,马老师脸如冷霜,嘴里喷出的却是烈火,火势直接向我冲来:“刘福琪,前边来,站着!站好!”
全班都愣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马老师打开我的作文本,照本宣科地念起来。三、四句话内,竟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一气之下,马老师把我的本子摔到讲台桌上,训斥道:“都高等生了,说出来的话,还不如个吃奶的孩子。”
我觉得委屈,更感到莫名其妙。但那个年代的孩子,尤其农村的孩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没有丝毫反抗和叛逆意识。好不容易忍到下课,拿过作文一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由于作文时感情太过兴奋,前四、五行里竟丢三落四少写了七、八个字。休言精彩,连通顺二字都谈不上了。我把脱落的字补齐,怯怯地交给班长,想请马老师重新审阅。
下午,自习课上静寂无声,谁也没有注意到马老师什么时候走上讲台的:“停一下,同学们。”
大家抬起头来,见马老师拿着作文本的手在明显颤抖,声音的颤抖与手同拍节:“我,马伟骏,首先要向上午受了屈辱的小福琪赔礼,道歉,鞠一躬。”说罢,真的转身向我,深深地弯下腰去。我腾地站起来,泪流满面,哽哽咽咽吐不出一个字来。
马老师继续说:“这篇作文,比上午那两篇范文要胜出两筹。因为批改时我正犯痰喘,见前几行念不成句子,庄稼火一发,就扔到了一边,白白冤枉了一个好孩子,玷污了一篇好文章。罪过!罪过!现在,小福琪这篇作文,我要重新讲评。”
我注意到,马老师通读我的作文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弥漫着极其严肃的气氛。朗读声停,一片掌声。马老师总结道:“这篇作文最大成功点,全在于‘真实’两个字。事情真实,人物真实,感情真实。金玉大姐是小福琪最挂心的人,他跟金玉大姐的感情,是从这里(马老师指指自己的心口)流出来、冒出来的,不是从这里(马老师以手摸摸自己的胳肢窝)挤出来、压出来的。”——他又恢复了幽默风趣的常态。
马老师呀,学生对你的思念,此生此世,永不泯灭。陈金玉大姐姐,你当初到达了朝鲜没有?你现在在哪里呀?
(见于2019.6.27《中老年时报》)